下面我讲一下社会生态学家到底做些什么,以及应该做些什么。
首先,社会生态学家要带着问题观察社会和社区:发生了什么“不是所有人都知道”的变化,什么是“范式变迁”的变化?第二个问题:有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场变革而不是一种潮流?要测试一下:变革有什么效果?换句话说,变革使哪些领域发生了变化?最后还要问:如果这是一场真实有意义的变革,那么它提供了哪些机会?
一个简单的例子是,知识成为重要的资源。就我而言,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《士兵福利法案》提醒我变革已经到来。这个法案要求给所有退伍老兵补贴,资助他们到大学学习。这是个史无前例的举动。事后看来,《士兵福利法案》促进了知识社会的来临。但是在1947年和1948年,没有人说出这个观点。我当时反问自己:“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台《士兵福利法案》,是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?人们是否会珍惜上大学的机会?”很显然,虽然1918年的美国对老兵也非常慷慨,但是当时肯定不会给老兵提供上大学的资助。假如1919年《士兵福利法案》在国会通过并实施——这根本不可能,估计也没人愿意上学。当时,上大学不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,只是富裕人家的专利,而他们不需要《士兵福利法案》的资助。聪明但家庭贫寒的人也选择上大学,但贫穷不会影响这类人的学业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高中教育是必要的,但大学教育还不流行。
这就引向第二个问题:“教育对人们的预期、价值、社会结构、就业等有什么影响?”一旦人们提出这个问题——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问这样的问题,就表明知识已经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地位,首次成为人类历史上创造性的资源。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美国社会处在变革的边缘。
又过了十年,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,所有人都在讲“知识型社会”和“知识型工作”是经济的新中心,“脑力劳动者”是新式劳动者,并且是占据优势的白领。
社会生态学家的另一项工作,是他必须关注影响。社会生态学家的目标不是知识,而是正确的行动。从这个角度看,社会生态学是一项实践,如同物质世界中药物的作用。社会生态学有两个目的,一是平衡连贯性和保守力量的平衡,二是保证变革与创新的协调。它的目的是构建动态平衡的社会,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且具有凝聚力的。
为了达到目的,社会生态学家的文章读起来必须轻松。这首先要排除“旁征博引”。事实上,“旁征博引”在社会生态学中会显得极不协调,“好学多知”也会让人反感。自以为是地声称科学不够“科学”,并不是“尊重”,而是说明科学不够普及,是一种蒙昧主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,美国的一流学者,尤其是社会和政治学者都是为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写作,比如当时一流的历史学家莱因霍尔德和尼布尔、玛格丽特·米德和本尼迪克特。马克斯·韦伯的文章文风简洁、深入浅出,刊登在杂志或报纸上非常吸引普通读者,凡勃伦的文章也是如此。
法国哲学家朱立安·班达(1867-1956)1927年出版了《知识分子的背叛》一书,猛烈抨击当时的知识分子,认为他们为了追逐潮流而违背责任,用种族主义煽动民众,鼓动纳粹投人其运动。随后十年,欧洲知识分子——不只是德国知识分子——的情况印证了班达的判断,他们狂热地支持希特勒,还近乎崇拜地支持斯大林。
我认为当今知识分子的暧昧态度,也是一种逃避和背叛。知识分子对文化水平的下降负有责任,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。知识分子认为是读者不愿意接受知识、科学、交流辩论和理智,但是现实显然不是如此。但凡学者写出优美的散文,总有大批追捧者。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历史学家中的芭芭拉·塔奇曼,生物学家中的雷切尔·卡森或罗兰·艾斯勒,社会学家中的霍维兹,还有很多其他学者都把专业知识写得深入浅出,读者众多。读者依然是以前的读者,水平也不低于从前。只能说,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只剩下傲慢和自负,别无他物。
但是社会生态学家应该具有一些傲慢和自负的心态。他们的工作不是创造知识,而是为人们构建愿景。社会生态学家必须是一个教育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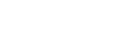
 问答
问答 创业社区
创业社区 创业学堂
创业学堂 讲师团
讲师团 我
我




